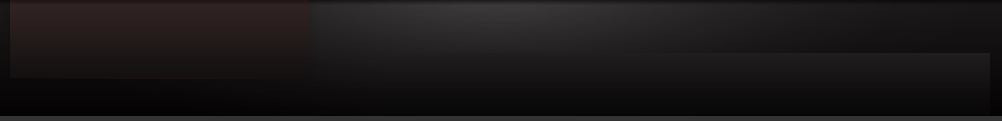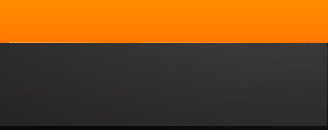天聚注册-首选链接发出的动静太大,殿外太监宫女乌压压跪了一地,颤巍巍问:“陛下,娘娘,可有事?!”
“无事。”我和他异口同声地说,帝后打架,传出去实在太难听,更会招来百官唾骂。
我用力地一把将他压制住在我身上的高大躯体推开,再暗中狠狠地掐了掐大腿上的软肉,眼泪疼得流出来,我抽抽噎噎,装成十分委屈:“楚怀!你还要欺负我到什么时候!”
他坐在我的身旁,平静地整理好被我扯乱的衣袖,漆黑如墨的碎发从玉冠里散出,垂在白皙的颈间。他清逸沉静的脸上流露出嘲讽的笑意,寒星似的眼眸微眯,淡淡道:“宁遥,你是被人欺负去的性子吗?”
不行!我定了定神,今日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就算再来哄我,也是不能够。
我腾地一声从地上站起来,向着外头喊道:“灵鹊儿进来,我们收拾东西回云州!”
我应了,叉腰指着殿内的东西,锦衾罗衣、金珠钗鬟:“这几样不要,其他的通通带走。”
在整个过程中楚怀就坐在那里,不为所动地旁观着我和灵鹊儿忙忙碌碌用包袱装东西。
如同少年时我总参不透他的心思,现在他已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帝王,心术之深,更不可知。
而我的心却越来越沉,手心中不断渗出黏腻的冷汗,太过湿滑,几乎快拿不住东西。
小胖子楚年年此时散学归来,迈着小短腿艰难地刚跨过门槛,还来不及放下小书包。
我拍掉手上沾到的灰,趁机捏几把他圆圆白白的脸蛋子,耐着性子跟他解释:“你娘我呢,马上就要卷铺盖走人了,回云州去找你舅舅收留我。年年乖啊,去找你爹要吃的去吧。”
小胖子动作敏捷,双手双脚死死扒住我的腿,嚎啕大哭如同魔音灌耳:“娘啊,你不要走,要走也要带着我一起走,不可以丢下我一个人的。爹爹好凶,我害怕,呜呜呜。”
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没娘的孩子是颗草,有娘的孩子是个宝,把自己讲得多惨似的。
不至于,应该不至于。我悄悄地睁开一只眼偷看楚怀对此的反应,见他终于起身走了过来。他一只手可以轻轻松松地拎起楚年年,像拎一只小狗那样简单,他冷声问:“老子很凶?”
小胖子憋嘴傲娇地哼一声,楚怀修长的指节在他额头上敲了一记栗子,让他重新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我顿时感到有些窘迫,闹过一场,不知如何面对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缓解尴尬。
我开始努力想怎样才可以让自己作出不那么在乎的模样,不至于让自己输的那么惨。
蓦然间,他附身拥我入怀,嗓音暗哑,“阿遥,今生今世我楚子慕只会有你一个妻子。”
谢朝槿,谢朝槿,这个从我十四岁起第一次见到楚怀,就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名字。
有做丞相的父亲与做中宫皇后的姑母,她甫一出生,便是命定的太子妃,一生遂顺无忧。
我幼年丧母,生长在边境云州。爹和哥哥很忙,常年领兵在外,我无人管教,不知诗书礼乐,名门淑女们要学的东西,我一概不会。我又怎么跟她比呢?又怎么可能让楚怀喜欢我呢?
至少我们之间还有楚年年这个孩子作为维系和宁氏举全族之力助他登上皇位的恩情。
暖日和风的午后,楚怀和我沉默的一起用完午膳后,他回到勤政殿继续处理堆积的政务。
我坐在窗子边看书,渐渐感到一阵凉意,推开窗一看天阴阴的,原来已是下了一会的雨。
我伏在桌子上,头埋在臂弯里。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是想家了,想爹想哥哥,眼睛很酸,眼泪控住不住地流出来。
高山上的雪化开,清澈见底的雪水从山涧中潺潺流出。溪中带来上游如绯的落花,软软浓浓的新绿一夜而来,风吹过繁盛的牧草,像翻涌的海浪。
纸鸢拖着长长的尾翼在风中坠落,哥哥宁远在不远的小山上挥手唤我,“遥遥,快过来!”
他领兵驻扎在外,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我高兴地飞奔过去,腕间坠着的金铃琳琅脆响。
那也是此生我第一次见到楚怀,那只纸鸢正静静地躺在他的足边,他附身替我拾起。
风拂尘徽,三千日光。十五岁的白衣少年唇红齿白,他一双潋滟的黑眸是寒潭里倒影的星子,清逸翛然的模样仿佛天上落下的仙人,他无疑是我十四年里见过最好看的人。
我的心就像那破了个大洞的风筝,呼呼作响,快要跳出喉咙,甚至感到丝丝的痛意。
从来不知愁滋味的我,在那个瞬间才知晓原来喜欢一个人不仅仅是欢喜,居然还会心痛。
我羞红脸从他手中抢过纸鸢转身就跑,哥哥在身后大喊:“小妹年幼无礼,请殿下恕罪。”
后来我才知道他穿白衣是为了给他的母亲,被废黜赐死的废妃守孝。他来云州更不是为了游玩,而是遭到圣上的厌恶,被驱逐出京到了大宁最偏僻的云州,让其自生自灭的。
我爹一直告诉我,做皇帝就是要爱民如子的,可是为什么皇帝对自己的亲儿子这么坏?恨不得让他死掉。我无法理解,怎么爹和爹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呢?
要好到让他喜欢我,离不开我,让我当他的娘子,要能天天看着他的漂亮脸蛋多开心啊。
他从书案后抬头,声音比山涧雪水更加的清寒,清冷彻骨:“宁小姐,下次不必再来。”
“为什么?”我执拗地问,我才不要听他疏离叫我宁小姐,我想听他叫我遥遥或者阿遥。
楚怀不答,神情冷峻,身形快得看不清。他豁然站起,推开阻隔的书案,一把将我拉入怀中,飞速退后一步,铮——
我虽是武将的女儿,但也从未见识过如此刀光剑影的景象,恐惧的眼泪本能地流出。
却又因他的一句别怕,泪硬生生地憋在了眼眶中,可怜兮兮地点头:“好,你不要有事。”
楚怀不等我回答,已抽出佩剑与破门而入的刺客缠斗起来,眉目凛冽,杀招狠戾。
奈何对方来势汹汹且人多势众,楚怀一人渐不能敌,鲜血染红了白衣,他咬牙坚持。
我躲在墙角看得分明,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大勇气,举起一旁的花瓶奋力向着刺客的头上砸去。
花瓶碎的四分五裂,那刺客身形一僵,额头流血,怒目圆睁,转身拿刀向我狠狠地砍来。
刚才砸花瓶的举动已经耗尽我所有的力气,我软软地瘫倒在地,看着刀刃袭来不知所措。
我凄凄惨惨地想,果然色字头上一把刀啊,男色也是色,古人诚不欺我!如今我就这样死了,还没做成楚怀的娘子,忒亏!
原来是哥哥领着护卫赶到了,我看见楚怀好看的脸上污染了血迹,秾艳的像春日原野上绵延不绝的花,美得惊心动魄。
我醒来时灵鹊儿正守在我的床边哭,我怕我再不醒来,她的眼泪就要先把我淹死。
“好。”她站起来拎起茶壶去给我灌水,但很快她气呼呼地走回来怒道:“害人精来了!”
楚怀走进来时,我躺在枕头上极力装成娇弱的病美人模样,青丝虚掩,眉间若蹙。
他开口还是那冷淡而疏离的称谓,但语调委实软了许多:“宁小姐,多谢你舍身救我。”
“谢就不用了,让我当你的娘子吧。”我开门见山道,又觉得自己太过直接,娇羞垂眸。
成亲这种大事其实可以等到我及笄后再说啊,于是我假装怯怯地拉住他的衣袖,摇了摇央道:“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以后叫我阿遥,好不好?”
他顿住,闭了闭眼,艰难启齿:“阿遥。”像是从唇角挤出来一般,但声如珠玉轻响,很好听。
楚怀抽回我手中的衣袖,薄唇紧抿,冰冷的脸上罕见地流露处哀伤的神情,阴云笼罩。
我心中浮现处一个很不好的念头,背脊发寒,脱口道:“啊,不会是?!圣上……”
“不要说。”他话语中竟染上几分哀求,止住话语,哀求我不要说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实。
他薄唇嗫嚅,终是倦倦道:“皇家的事,很可怕吧?太脏了,我希望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他的父亲贵为当今大宁的天子,杀了他的母亲还不足够,居然还要杀掉自己的儿子。
世人口中艳羡的天潢贵胄,不应该是鲜衣怒马,潇洒恣意的吗?为何要对楚怀如此残忍?
我伸手握住楚怀的手,愤愤道:“你放心,以后在云州,有我在,就没人敢欺负你。就算是你爹也不行!”
他闻言微笑,笑起来时仿若光华初绽,揉了一把我的乱发,笑道:“那你得快些好起来。”
骂到最后他自己先老泪纵横起来,哭道:“遥遥,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叫我将来到了地下如何跟你娘交代。你以后不许再去找昭王殿下,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我认错的态度良好,但等身子大好以后,依旧继续去找楚怀,把我爹气得天天在家骂他。
我们一起去看原野上的星空,漆黑的天幕上银河耿耿,四野开阔,仿佛近可徒手摘星辰。
少年仰望天幕,久久不语,唯有草叶间蛰伏小虫的低鸣声传来,而我悄悄凝看他的侧颜。
我爹也只得感叹一句,女大不中留,将我交到楚怀的手中,让他一定要好好待我。
那夜红烛高烧,鸳鸯戏水的红盖头揭开,喜服加身的楚怀在柔暖的光晕下俊美如玉。我羞涩不已,心跳加速,不敢看他含羞道:“楚……夫君……你可喜欢我?”
答非所问,他不说喜欢我,却说今生只有我一个妻子。我指尖一颤,挽出一个傻傻的笑。
圣上重病沉疴,命太子监国,又恐太子年少,压制不住底下人,另下旨让谢丞相辅政。
然地僻如云州,人们还不能切身体会到这种变化,日子还是照常过,不曾改变分毫。
那时我刚怀了楚年年,情绪不稳,变得娇气十足,临近晚间我突然很想吃西街的糖葫芦。
让楚怀给我去买,他一边骂我矫情,一边骑马出门往西街去,但这一去很久都没有回来。
我在府中急得不行,直到我爹派人给我传信说楚怀在他那里,让我不要担心,早些安寝。
刚到门首,道边堆积着残雪,冬日没有一丝暖意的晨光正照在策马归来的楚怀身上。
他似在走神,下马时见到我才露出极其疲倦的笑意,冰冷的手握住我的手问:“阿遥,如果我要做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甚至可能会死,你会不会支持我?”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点头,“子慕,我是你的妻子啊,不论什么事,我都会陪着你的。”
哥哥来看望我时,对我说出了内情,“当年派人来刺杀殿下的人不是圣上,而是谢家。”
虽然有些生气,他这人怎么当时跟我说假话呢,明明是谢家捣的鬼,他却骗我是圣上。
哥哥点头道:“还是谢皇后那个谢,太子妃谢氏的谢,那谢氏一门可谓富贵已极了。”
我屏气凝神,听他继续道:“携家人多年来把持朝堂与后宫,广布党羽,有不臣之心。圣上受其挟制,只能装出厌恶的模样,用计将殿下贬到云州,云州天高皇帝远还未渗入谢家的势力。圣上打算让殿下借助我们宁家的兵力,夺回皇权,密诏在几日前送到了父亲手中。”
爹和哥哥全都披坚执锐亲上战场,爹甚至重伤了一臂,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拿起刀戟。
我扶着肚子轻轻地蹑足走进去,将熬好的参汤放在一边,未出声先帮他整理凌乱的书册。
眼尾扫到狭缝里的木匣子中珍重地藏着一枚精致的绣囊,浅粉色的缎面上绣着一朵美丽的木槿花,在一旁绣着两句诗,“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很精巧的女子之物。
云州兵马攻破帝京的那一日,寒光照甲,圣上拖着病体挽住楚怀的手,老泪纵横。
我那时知晓了,哦,那朝槿原是太子妃谢氏的闺名,谢氏朝槿,名字同她的人一样美丽。
谢氏一族被诛,太子被废为庶人,和太子妃一道被囚禁在德业寺中,为大宁历代先帝祈福。
我看见楚怀的目光在人群追寻着她单薄的身影而去,忽然伤心地问,“你喜欢她啊?”
这不受宠的皇子与命定的太子妃的故事,或许是缘于深宫凶险异常,或许这位高门小姐某次的出手照拂这位皇子,他睁开黑眸望见她像救苦救难的神祇,像莲台上一尘不染的观音娘娘,心动于一瞬间。
哈,可是他要是希冀能够重返帝京,就不得不娶我,手握五十万重兵的云州节度使的女儿。这天大的恩情无以为报,只好通过联姻的法子,让下一任皇帝是宁氏女所生,让宁家得以成为最有权势的外戚。
谢朝槿一身素服入宫来谢恩,她不染铅华依旧貌美,纤腰楚楚地跪地,“皇后娘娘万福。”
袖口下藏着指节微动,灵鹊儿出声提醒,我定了定神微笑道:“阿嫂不必拘礼。”
我倒也没有让人下不来台的恶习,想想她也是可怜人,跌落尘埃,家破人亡,诸多的身不由己。
她说话时星眸低垂,半边侧脸优美,嗓音柔和,如果我是男子,保不齐连我都要心动。
其实她和楚怀还是挺般配的吧,哎,真是可惜,有了我这块绊脚石,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腹中绞痛撕扯我的五脏六腑,眩晕阵阵,算算时间楚怀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扶住桌角勉力支撑。
“皇上驾到——”正在这时,楚怀颀长的身影迈入殿中,明晃晃的日光在他周身镀了一层光晕。
我站起来去迎他,下一刻,鲜血大口大口地从口中呕出,我疼得直不起腰,直直摔倒在地。
很吵很吵,不得安宁,一定是楚年年这个孩子在我耳边痛哭流涕,“阿娘,你不要死,呜呜……”
又听见楚怀嘶哑道:“阿娘生病了,需要休息。你不要吵她,先回去念书,乖。”
混乱中太医来了几波又走了几波,最后彻底安静下来已经过去了好久,我真的太想好好的睡一觉。
“阿遥。”楚怀一直没离开,他轻柔抚过我额前的碎发像在心中漾起雨后的涟漪,低低道:“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是对不起他无法对我付出和我一样的同等爱意。还是对不起分明是谢家派人来刺杀他,他却骗我说是圣上派来的人,博得我的同情后,让我曾以死相逼让我爹对他鼎力相助?
我回想当初,那时爹守卫云州边陲已经快有二十年,一直选择的是明哲保身,不欲卷入皇权的纷争。
“子慕,要不要我去问问爹?”我看着楚怀变得日渐沉默,深敛眉眼,忍不住轻声问道。
切,在我即将生气的最后一刻,他将我揽到怀中,凉凉的指尖戳下我鼓起的脸颊:“阿遥,谢谢你。”
他皱着眉说:“遥遥,你就不怕将来楚怀做了皇帝,他会有很多嫔妃,你将不会是他唯一的妻?”
“哎,你懂什么,傻孩子。”爹无奈叹息道,“你回去吧,告诉楚怀,我答应他了。”
那时,我只要楚怀给我买一根糖葫芦就满足了,又何曾想到我们中间还夹着一个谢朝槿呢?
我说过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但他的良心好像仅止于此了,给了我一个空荡荡而名正言顺的妻位。
喉头灼热逼人,腥热的鲜血再度从胸腔内涌出,我疼痛难忍拼命挣扎起身,伏在榻上又呕出一地的红。
楚怀将我揽入怀中,轻轻拍我的背脊帮我顺气,我死死拽住他的衣袖,惨笑道:“我这是怎么了?”
“是谢朝槿。”我睁大眼睛,喉咙如同被刀子划开般的痛,“我喝了她递过来的那杯茶。”
他不信我。明明我昏睡过去前,已经示意灵鹊儿将谢朝槿给我下毒的证据呈上,可他还是不信我。
而我几近祈求地说:“子慕,我才是你的妻子,难道你觉得是我在陷害谢朝槿吗?”
楚怀蓦然道:“你以前不是说过,不论什么事,你都会陪着我的,会都信我的,我说了不是谢朝槿。”
他诱哄道,“你先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你不是想家了吗?等过些时日,我让你哥哥来看你好不好?”
我别过头不响,他起身唤来灵鹊儿,让她好好照料我,服侍我按时吃药,说完便离开了殿中。
我再也无法忍受,压抑的细碎哭声终变成放声大哭,我可真没用,在他心里永远比不上谢朝槿。
灵鹊儿满脸担忧地看着我,一碗药捧了老久,“小姐……你这样若是让老爷知道了他该有多伤心。”
我伸手接过直接一饮而尽,血沫混着极苦的药味在口中蔓延开来,闭眼道:“我要睡了,你先去忙吧。”
那之后坤宁殿中的宫人们被调走了大半,一时门庭冷清,有关帝后失和的传闻渐渐在宫内外传开。
我因着养病的缘故,不能随意出去走动的缘故,只得整日窝在殿中,教教楚年年读书写字。
灵鹊儿起初还颇为生气地跟我告状,说楚怀给谢朝槿又赏赐了什么奇珍异宝,又带她到哪里去宴游。
那些过去他与她来不及做的事情,他都在竭力弥补,毕竟他可不再是任人欺凌的皇子,而是皇帝啊。
楚怀现身殿中,我微微一愣,隔着扶疏的花影,我们已经快有月余没有见过了面。
彼此之间竟有一种无言的生疏生了出来,最后还是楚怀先说:“阿遥,近来可好?”
楚怀毕竟是个皇帝,后宫佳丽三千本是寻常不过,“陛下准备给谢氏什么封位?是贵妃?还是皇贵妃?至于大臣那边,我可以试着去说说情……”
“宁遥!”楚怀怒不可遏打断,眼皮上泛起一抹潮红,“朕竟然不知道皇后何时变得这么大度!”
又胡乱发什么脾气?我被他突然的吼声吓到,娇嫩的花枝在手中硬生生折断,真是可惜了。
我不知为何变得越来越嗜睡,唯有楚年年来找我的时候,才得以勉强打起几分精神。
朦胧中见一个纤细的身影坐在床榻的矮机上,我以为是灵鹊儿,就问:“是什么时辰了?”
“酉时。”那人答道,是个略熟悉的女声,然后她有些古怪的笑起来,“你可看清我是谁了?”
我眯了眯眼睛,这时将晚的夕光正穿门入户,堪堪照清楚那人的面容,显露出一张极美的芙蓉面。
赫然是谢朝槿。我心中怒火猛然腾起,好啊,我忍气吞声的不去招惹她,她倒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刚想骂她不要脸,就这还世家名门出身的贵女呢,奈何情绪激烈,眼前又是一阵旋黑。
谢朝槿轻笑:“你如今中毒已深,还省省力气的好。你若是想活命,不如先听一听我的条件?”
我缓了缓气并不作声,其实那日我已经发觉她递过来的茶水不对劲,气味过于甜,但我还是喝了下去。
一来那毒我并不陌生,是云州山谷内一种常见的植物炼成,虽然毒发时看着十分吓人,但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危害。二来我就是想让楚怀看清楚,这位他放在心尖尖上的姑娘,是多么的阴险恶毒。
可她说我中毒已深,究竟是何处不对?眼下与她硬拼着实没什么胜算,我皱眉示意她继续说。
“我不是真正的谢朝槿,真正的她早已经死了,你不必将怨气撒在我的身上。”她淡淡道,“我是谢家大公子手下培养的死士,奉命扮做谢朝槿的模样,用以迷惑帝王。你晓得的,谢氏一族虽然在明面上被诛,但这样绵延百年的大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朝堂后宫之中,还有许多我们的人隐藏在暗处。”
“我原以为我装得很好,哎,原来皇帝早就发现了我是假的了,他骗我,我骗他,真好笑。”她低声轻笑,“我们收到的消息,你家哥哥已经在带兵马进京的路上了,而皇帝前日在狩猎的林中,忽然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他早谋划好了要和你哥哥暗中联手声东击西,所以在这里拖住我,是等你哥哥来。不过这也没什么难的,既然我可以扮成谢朝槿,就可以找人可以扮成皇帝的样子,潜入宫中。”
“你要做的很简单,你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到时候见了你哥哥,你只要认定宫里头的这一个才是真正的皇帝的就可以了。如果你同意,我便给你解药,让你到时离开帝京,便能好好的活下去,如何?”
见我躺在枕上眨了眨眼睛却没有说话,她声音变得阴冷像寒风刮进骨子里:“毒发的滋味不好受吧?”
像无数虫蚁钻进身体一寸寸啃咬血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纾解的致命疼痛,折磨得人将近死去而不能。
我呼吸一窒,想楚怀不见得有多么喜欢我,我又真当值得为他去死吗?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我死了爹和哥哥一定会很伤心,还有可怜的楚年年小小年纪就要没了娘亲,为了楚怀值得吗?
“好啊。”嘴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我扬眉轻声笑了笑,她玩味地问了句为什么。
我答:“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我又不傻。而且既然你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我又何苦挣扎,但愿你们可以说话算话。你刚才说我中毒已深,这是何故?”
她点点头,“这是半份解药。”说着从袖中拿出一颗药丸喂我吃下,“你之前曾受过重伤,还记得么?那刀口的上涂有一种毒残留在你的体内,但若遇上我下在茶中的毒,便会衍为剧毒。”
他孤身一人只带了一个侍从入宫先来看我,我不得不画了极浓的妆容掩盖掉恹恹的病容。
我还如小时那样依偎在他的身旁,言笑晏晏地同他讲我近两年来在宫中都干了什么事。
哥哥静静听着,偶尔附和一二,待我说完,才正色严肃问:“阿遥,京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欲言又止,盯着我看了许久,盯得我心中发虚,方说:“好,天色不早了,去赴宴吧。”
假楚怀坐在我的身侧,语调柔和地问我可要吃这个或那个,还嘱咐我不要喝酒,对身子不好。
我几乎在沉醉在这样一种温柔的假象里,然而微风拂过,在肌肤上起了一层鸡皮栗子,我很快清醒了一瞬。
这些年,虽然我和楚怀温情的时刻也有过,但总还是吵架的时候多,吵到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酒过三巡,哥哥似乎快要不胜酒力,半醉地握不住手中的酒杯,坠地后酒液倾洒。
我刚要出声,那本该守卫宫城的禁军却冲进来纷纷抽出刀刃,刀光剑影在烛火下变得格外刺眼。
文武百官惊恐地面面相觑,包括我身边的假楚怀也神情难看到极点,撑着桌角站起。
哥哥不复刚才醉酒的模样,转头看向他带入宫来的侍从,清楚的凛冽道:“这话不应该问我吧?”
那侍从正在此时抬起头,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明晃晃的光照在他的脸上,居然又是一个皇帝!
“哈哈哈——”几息过后,反倒是假楚怀先笑起来,“宁将军哪里找来与朕如此相似的人?若是一不小心,连朕的皇后可能都要认错了,皇后,你说是不是?”
那毒又发作起来,冷汗从额角坠下,我强忍疼痛微笑道:“那臣妾走近了,好好看一看。”
我呼出一口气,告诉自己,宁遥在坚强些,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你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但刚迈出一步,却被他用力地捏住了手腕,喝令道:“不必看了,宁将军,替朕杀了这个人!”
我心惊胆战,仓皇间看向阶下一身素服的楚怀,他有漆黑俊美的眉眼,姿如玉树,视线与我相触碰。
那是我从少时就心心念念的人,喜欢成为了一种本能,就算他不喜欢我,我终究是硬不了心肠,不能亲手杀死我少年时的情意。
却有一人率先冲出来拥着了我的身体,清清淡淡的气息,似恍然间云州苍朗干净的月色升起。
鲜红的血从我的唇中涌出,我从楚怀的怀中抬起头,嘶声力竭地喊:“那个人才是假的!”
“宁遥!”向来沉着冷静的男子声音变成了一种凄厉的腔调,荒腔走板,像人死之前唱的挽歌,“你别装病了,快起来!快起来啊,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信你好不好?”
我知道那是楚怀在跟我讲话,我想告诉他,这一次不是骗他的,是我真真真切切的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淅淅沥沥的雨珠滴落在我的面颊上,我最讨厌下雨天了。这雨却是温热的,分明是楚怀的泪。
“你这个傻子……”楚怀那俊美的脸哭得竟如此的难看,但他说的二字,如此清晰。如雷贯耳。
他说父皇已经害死了阿娘,他不能再把我一个孤零零留在这里,再让人把我也害死了。
祭礼上灵鹊儿姑姑抱着我哭,我们两个抱着哭成一团,那时我还太小,只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阿娘了。
舅舅忽然不顾君臣之仪,冲上去与父皇扭打在一起,他说,都是父皇的惊疑猜忌才害死了阿娘。
他还说父皇就是一个懦夫,是连喜欢都说不出口的懦夫,因为他需要阿娘一次次对他心软。
父皇被舅舅打到在地,仰望着空荡荡的上空,那痛苦的哭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父皇甚至没有杀掉给阿娘下毒的那个女人,他逼她给出阿娘的解药,父皇不肯相信阿娘就这样死了。
可那女人却讥笑说:“不论如何她都是要死的,我们一开始就没想让她活下去。没想到,她却是个不怕死,哈哈,你为了骗我,那样伤她,装得那样情深意切,她还是拼了命助你,你是赢了,但你好过吗?!”
惨叫如裂帛般惨烈,灵雀儿姑姑赶忙捂住我的眼睛,从她颤抖的指缝处,我看见父皇杀掉了那个女人。
我渐渐大了,大概能够理解父皇那种生长于残酷宫廷中,随时面临死亡的阴影,养成的猜忌隐忍性子。
他需要阿娘爱他,但他却也怕宁家成为下一个谢家,将他的爱隐藏在心底,才让阿娘误会他这么深。
父皇临终前,我陪在他的身边,我看见他浑浊而苍老眼睛盯向虚空,喃喃道:“阿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