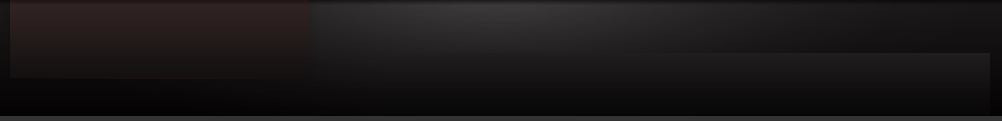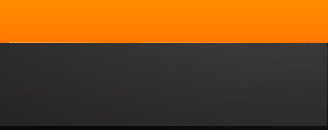首页雅米娱乐平台她那几颗忍不住的泪,还是缓缓地顺着泪沟淌下来,晶莹剔透地挂在脸上,欲坠不坠。
父兄新丧,无法守孝,尚且是热孝期间,就得为了活命,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舍去身体与清白。
不遇良人,一生凄苦,分明是早已定下婚约的未婚夫,却对她没有一点情分,如今看着他,好像一眼就能望完自己的后半生。
“我在想那位江姑娘经历的事情,越想越觉凄惨,越想越觉悲愤,实在无法想象人间有如此惨事,就忍不住哭出来了。”
以前,此事刚发生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听后泪流满面,义愤填膺,愤怒到恨不得当场将孟允章挫骨扬灰。
他看着沈柔,难得劝慰道:“事已至此,不用太伤心,不如写好你的戏文,让全天下人都去辱骂孟允章,为她伸张正义。”
可是,不知为何,大颗大颗的泪珠,却不受控制一般,滴落到纸上,晕花了写出的字。
卫景朝放下笔,娓娓道来:“当初你即将及笄,我便拟了字递给平南侯。只是平南侯顾忌你的名声,虽定了亲,但没有成亲,总不好来往太密切,便没有告诉旁人。”
长公主对外解释说,希望仲也的品行与才华如同直径一寸的明珠一样稀世罕见,在黑夜中如月亮一样皎洁明亮,耀眼无双。
她在书房里坐了一天,笔耕不辍,认真思索,认真写了一整天,终于写完了第一折戏文。
“这是第一折戏文,讲的是江燕燕有个未婚夫,感情甚笃,恩爱至极,于上元节相约赏灯,不料偶遇齐王章昀,惨遭调戏。”
却在春日游湖时,偶遇孟允章,从此被这么个恶心玩意儿惦记上,想想就觉得恶心。
要卫景朝来论断,哪怕是她那位传闻中惊才绝艳,风华卓然,京都第一的兄长,恐怕论起文采精华,也未必比得上她。
单只看这戏文,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偏偏又不全是市井白话,其中化用的典故,使用的意象,哪怕是不懂的人,也不会看不明白。
与未婚夫见面时,她提着荷花灯,拉着他的手臂说,“等今年夏天,荷花盛开时,我就能嫁给你了。”
诚然,满天下有很多人会写戏文,尤其是他手下的幕僚,个个才华不俗,都是使文弄字的高手。
而沈柔,识文断字,过目不忘,写得一手好字,做的一手好文章。今儿写出的戏文,不比任何人差,直接拿去给戏班子唱,也必定高朋满座,满堂喝彩。
沈柔珍惜地接过他手中的纸,在桌案上捋平了,放整齐后,抬眼看向他:“这个放在哪里?”
卫景朝抬手,从书柜上拿出一个盒子,将那一沓纸反着放进去,合上盖子,上了锁。
谁知道,沈柔却摇了摇头,小声道:“我不要你的钥匙,我只管写,保存是你的事情。”
他大概也是明白,她为何不肯收。是怕稿子丢了,或者泄露了,他怀疑是她所为。
“柔儿最喜欢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知道长公主素喜牡丹,侯府中向来不种其他的花,但柔儿既要嫁过去,你可否让人在她的院子里挖个小池塘,种上三五十株荷花,也算是个慰藉。”
这池塘,就挖在他院子里,里头种了千株荷花,前几日他回家时,那些荷花刚长出嫩绿的叶子,尚且娇嫩。
卫景朝盯着那些荷叶,闭了闭眼,对身后的陆黎道:“将这些花,都移栽到鹿鸣苑去。”
陆黎伸头看一眼,嘀咕道:“侯爷,这不是老侯爷给您的东西吗?您准备拿去哪儿?”
就好像这一次,沈柔好像什么都没做,只是按他的要求,写了一出精彩绝伦的戏文。
他看了后,明知文里虽没有他,字字句句都在说他,却只觉惭愧,只觉得对不住她。
沈柔躺在榻上,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感觉到有人躺在身旁,悚然一惊,顿时清醒过来。
以前,别说只是一出戏文,便是有人当着他的面,哭断了肠子,他也不会心软半分。
饶是寄人篱下,没有地位,她也忍不住恼了,深吸一口气,问:“侯爷有事吗?”
踏歌笑吟吟道:“陆黎带着人又挖了个池塘,就在夕照园后面的花园子里,等挖好了,姑娘推开后头的窗,就能赏风景。”
这么一想,踏歌不由劝道:“姑娘昨夜辛劳,再休息一会儿吧,侯爷今儿大朝会,没这么早回来。”
诚如踏歌所言,卫景朝没那么快回来。沈柔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写完第二折戏文时,天色已黑沉,才听见门外的马蹄声。
卫景朝在椅子上坐下,仰头望着房梁,慢慢道:“沈柔,今日廷议,提到了你的父亲。”
凭圣上对平南侯府的恶意,沈柔绝不相信,今日廷议,会有半句关于父亲的好话。
他缓了缓,道:“是为弹劾我。有人说,平南侯犯下谋逆大罪,我以前与他们父子来往甚密,又有翁婿之亲,难保没有参与其中。”
全天下人人都看得出来,平南侯谋逆一案,疑点重重,草率至极,摆明了是栽赃陷害。
卫景朝与父亲是有翁婿之亲,可他今年不过弱冠,往年也不常在京中,与父亲一年见不了三次面。
卫景朝如刀削斧劈的脸庞在灯光下格外清晰,此刻带了三分寒,三分笑,四分漫不经心。
“沈柔,气急败坏是小孩子的行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是蠢货的行为,逆来顺受是弱者的行为。”
她的父亲忠君爱国,正直刚毅。她的母亲温婉动人,善解人意。她的兄长玉树琼枝,浩然千里。
如果当时平南侯侯府被人污蔑谋逆,父亲的选择,不是听旨自尽,而是奋起反抗,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
他手中有数十万雄兵,反抗起来,哪怕是金殿里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沈柔,如果当初被指认谋逆的人是我,如果我手中有十八万人马,现在的江山,早就换了我来坐。”
章昀看见了江燕燕,沉溺于她的美色,不顾她已有未婚夫,便登门求亲,要江燕燕给他做妾。江燕燕不从,于是他便带了三十个壮丁,闯入江府,硬生生将人掳至齐王府。
她念白:“母亲啊,贼狼子恶贯满盈,稔恶不悛,还望母亲保重,活个日久天也长。待得日散云开,见贼狼子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母亲家祭,勿忘相告于我。”
江燕燕之母唱:“娇娥儿去虎狼穴,阿母偷生苟且,怎不叫我心扉痛彻。年迈人白发苍苍,送走我的女娇郎,地崩山摧难见面,怎不叫我悲云愁雾,泪千行。”
卫景朝几乎是认命般地叹了口气,“明日一早,我就遣人去边塞,给你母亲送去东西,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花这样大的篇幅,去写母女骨肉分离的情节,不就是提醒他,千万别忘了答应她的话。
沈柔自己心虚,便放柔声音问:“我虽有私心,但加一段这样的戏文,不好吗?”
那些罪名虽很大,说出来人人谴责,但其实并不是很能触动老百姓的心肠,他们听过,骂过,也就过去了。
她加这么一段戏。让听到的人,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子女,想一想自己的亲人,自然会感同身受。
沈柔醒时,他正坐在窗前,手握一卷书,却没在看,而是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虽说她什么事儿都干过了,主动脱衣裳也不是一次两次,还有一两次是大白天,但当着他的面穿衣裳,的确是第一次。
踏歌摇摇头,满脸无奈地转身走到卫景朝跟前,道:“侯爷,陆黎方才说找您有事。”
卫景朝一抬眼就知道她心里头在想什么,警告道:“再胡思乱想,明儿就把你嫁给陆黎。”
她是自小跟着卫景朝的,在他跟前素来胆大,不像别的侍女一样畏惧他,继续追问:“您到底是怎么看见的?”
那面镜子,摆放的位置,恰好在床榻与窗台之间,正对着另外一面墙,可以将屋内所有的场景都囊括进去。
沈柔失了遮挡,连忙扯过一旁的衣物盖住自己,露出一双又羞又恼的眼睛,控诉般地望着卫景朝。
她不知道卫景朝为什么突然要带她出去,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怕事情败露,引开麻烦。
两刻钟后,衣衫整齐地站在卫景朝跟前,双眼明亮,顾盼生姿,眼底盛满期待与欢喜。
贡缎铺底,青翠欲滴的翡翠做了棋盘,温润细腻的青玉做了书架,偌大的夜明珠做了照亮的灯具。
卫景朝微微蹙眉,在对面铺着虎皮垫子的矮榻上坐下,指了指手下的棋盘,慢条斯理道:“陪我下一局。”
她为自己辩解:“我只是觉得,你的手太有劲了,捏棋子的姿势,跟我不太一样。”
他却直接用了两个指尖一夹,棋子便稳稳当当地躺在他手心里,没有丝毫滑落的迹象。
卫景朝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指尖,又抬眼看看她绯红的脸,随手将棋子撂回棋盒里。
不过一刻钟后,他们绕过一处小山屏障,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山脚下一座幽静草屋,草屋外种满娇艳牡丹,牡丹丛中,一年轻男子正临花浇水。
裴晋阳平静道:“沈公于我有救命之恩,当日得知沈公出事,裴某多方奔波,奈何人微言轻,毫无办法,只能眼看恩公一家……”
沈柔闭了闭眼,“公子既然认识家父,当知父亲长相,既见了我这张脸,还有什么疑问吗?”
沈柔笑了一声:“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的身份。当日侯府被抄家,我连自己的衣裳都没保住,又谈何信物。”
裴晋阳沉默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起身,拱手下拜:“恩公之女在上,请受裴某一拜。”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哪怕她真的活着,哪怕卫景朝真的愿意娶她为妻,御座上的君王也断然不会答应。
如此深仇大--------------栀子整理恨,沈柔绝不能忘。谁知道,她的枕头风有多大的威力,会不会将卫景朝也策反?
明知他利用了她,算计了她,可她还是心怀感激,觉得亏欠于他,想找机会报答他。
就像今日,她分明不知道他为何带她来见裴晋阳,却还是在第一时间,就按照他的思路,去说服裴晋阳。
裴晋阳骤然想通其中关窍,猛地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声音悲痛:“圣人无道!圣人无道!”
卫景朝将茶盏放在桌子上,发出一声清脆声响,惊醒愤怒中的裴晋阳,他淡淡提醒:“慎言。”
裴晋阳双目发红,狠狠喘了几口气,看向卫景朝,“卫兄昔日所言,可还算数?”
原来,卫景朝是想要招揽这个人做幕僚,又得知此人与父亲的关系,所以才带她过来。
回程的路上,沈柔许是累了,神色恹恹地靠在马车壁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合上眼。
卫景朝望着她眉眼,主动解释,“裴晋阳出身河东,性格倨傲清高,又兼之父母早逝,被家族不容,便离族自居。”
她眉目间盛满懒意,又往后靠了靠,眯上眼,软声问道:“还有多久才到,我困了。”
但他终究是喜怒不形于色,只抬手捋了捋沈柔一缕散乱发丝,神态自然,堂堂正正。
侍女踩着小碎步走到沈柔跟前,轻声问:“姑娘醒了,渴不渴?饿不饿?想吃些什么?”
谁知卫景朝先冷笑一声,放下笔,盯着她,一字一句问:“你怎么知道,我没叫你?”
鹿鸣苑的二门到夕照园的卧室,足足有一里地,他是闲的慌,非得抱着个人走进来?
卫景朝盯着她小心翼翼的动作,嗤笑一声,“沈柔,凡事没弄清楚之前,别急着诬赖人。”
哪怕明知,长坏的骨头,只有打碎了重组才能救,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狠下心做这样残酷的事情。
卫景朝沉默不语。当初那件事传的沸沸扬扬,那个女孩从弘亲王府抬出来时,沈柔不曾见过,只是道听途说。
若是那一夜,他没有去看她。或者,他没有饮下那杯酒。又或者,发生那件事后,他没有答应接她出来,而是弃之不顾。
——如果那天进了明月楼的是旁人,是另一个可以救她于水火的人,甚至不用管是男是女,沈柔都势必会想法子利用对方,挽救自己。
事实上,从章昀骚扰江燕燕开始的那一刻,她那个“未婚夫”,就从整篇戏文里,消失了。
在沈柔最困难时,他一去千里,消失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帮上一点忙,没有一点用。
彼时不过十六岁,殿前策论时惊才绝艳,出口成章七步成诗,被誉为有“嵇宋之风”。
沈柔念:“硕鼠之皮,相鼠之仪!白耳之狌,独角之豨!蜥蜴为心,豺狼成性!狎邪无辜,残害弱质!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卫景朝搁下笔,轻笑一声:“若是我自己写,不出三日,全大齐人人都会知道,是我执笔所写。”
他脸上生出三分疏朗的倨傲,“纵翻遍整个大齐,也找不出一个人,能在文采上与我相提并论。”
盯着她的脸,见她始终平淡无波,好像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心里没由来生出一丝烦闷。
她抿唇,小心翼翼扯了扯男人的衣袖,声音怯怯的,试探道:“你……你不厉害?”
对上她一无所觉的天真眼神,卫景朝顿觉挫败,缓缓松开手,张了张嘴,终究是什么话都没说。
许久后,她慢慢开口,声音轻轻地:“我爹爹说,要把我嫁给世上最好的男儿。”
她盯着脚尖,没有看卫景朝,声音有些难过,“我们定亲时,爹爹说,卫家郎君虽年轻,然为人稳重,性情平和,卓绝有为,品行高洁。”
知道他高中状元,知道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成了一方重臣,知道他性格冷漠,知道他容颜俊美。
都怨卫景朝上值不稳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她总是记不清时日,觉得他日日都在休沐。
沈柔低下头,盯着脚尖,慢慢道:“是我僭越,想了不该想的,侯爷别生气,妾以后不敢了。”
平日里,她连装都装不好,一口一个你啊我啊的,丝毫没有人家外室姬妾的敬意和畏惧。
她没给人做过妾,也没见过别人家的妾,着实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她以后肯定会注意的。
卫景朝附在她耳边,声音清淡如雾,飘在半空中:“擦不好背,就从别的地方还回来。”
此刻,门外忽然传来踏歌高亢的声音:“奴婢拜见长公主殿下,殿下稍候片刻,侯爷正在沐浴,奴婢这就去通报。”
“通报?”女人的声音,是与卫景朝如出一辙的冷淡,“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再避开本宫?”
雾气氤氲,又隔着一层薄薄的屏风, 她看不清楚里头的情形,只隐隐约约看见卫景朝胸前趴着个身姿窈窕的少女。
此时此刻撞见儿子的事, 仍是尴尬得眼睛不知道该往何处放, 只觉进退维谷,手忙脚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半晌后,她轻嗽一声,已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匆匆移开目光,脚步散乱,转身退到门外。
经了方才的事,沈柔已经尴尬得抬不起头,一直将头埋在膝盖里头,说是再也没脸见人了。
长公主松了口气,开门见山道:“今日午后,圣上急招本宫入宫,有意为你赐婚。”
长公主叹口气:“本宫不懂,洛神到底何处不好,为何你百般挑剔?她既是公主之贵,又有掌权之尊,更是花容月貌,满京城想娶她的男人,能从宫城排到外城。只要她肯点头,那些个男的,给她做小也是愿意的,偏你不乐意。”
如今,若非卫景朝位列枢密副使的要职,又兼之掌管北疆官兵,洛神公主恐怕也不乐意跟他成亲。
哪怕是个死的,让她去结冥婚,只要给她足够的利益,恐怕这位公主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卫景朝手指把玩着腰间的玉佩,慢条斯理开口:“公主殿下将婚姻当做一门生意,我却不是那样的人。何况,纵使真的做生意,也该有我讨价还价的余地。”
长公主叹了口气,倒也没有劝他,只道:“若是不愿意就罢了,但你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否则陛下那边我不好交代。”
他不由想,若是沈柔知道他想娶妻的消息,明儿的戏文里,肯定就该出现,江燕燕的未婚夫为了不得罪齐王,另择高门贵女为妻,抛弃江燕燕的场景。
长公主终于没忍住,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他,半晌后才问:“是为了刚才那个女人?”
长公主闭了闭眼,也不乐意提起此事。最终,她只问了一句,“是哪家的女儿?若是身家清白,便抬进府中做个妾。”
有心教训他两句,只想起自己后院的莺莺燕燕,一时也拿不出话来说,最终只憋出几个字,“且注意着些。”
长公主终于没忍住唠叨,:“你怨我和你父亲关系不亲近,怨我们各自纳妾蓄养男宠,怨你父亲死时我没能回来,所以你一直不肯见我,我能理解。”
“只是,你早晚要成婚,如今小小年纪就花天酒地的,日后好人家的姑娘,哪个愿意跟你……”
长公主心知他不喜,也不敢多说,只能道:“为何要等等,总得有个说法,否则陛下日日要与你和洛神赐婚,本宫推得了一次,推不了第二次。”
卫景朝深吸一口气,不想与她争执,冷冷打断了她的絮叨,“你只对外头说,沈柔新丧,一年内我无意娶妻。”
长公主脸色变了变,蹙眉道:“沈家乃是谋逆大罪,他们家的事,你何必招惹?平白无故沾一身腥,有什么好处?”
欲成大业,除了兵、钱、权之外,最要紧的,便是一个“德”字。论语上说的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但等到天下人都称赞他有情有义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时,对他以后行事,会有莫大的好处。
“你有你的盘算,母亲听你的便是。只是仲也,你一向聪明,小心不要阴沟里翻了船。”
长公主向来只图利益,想到好处,便不再反对,只提醒他,“女人不像她们表面上那样柔弱无害,尤其是美丽的女人。”
她的儿子她自己清楚,一颗心是石头刻成的,肠子比石头更硬,血亲的弟弟妹妹都不曾放进眼里。
长公主明白他这是逐客的意思,无奈站起身道:“我今日过来,便只为此事,你既然心里有主意,我便先回去了。”
将人送出门,临上车前,卫景朝不咸不淡道:“母亲下次若再有事,让人喊我回侯府便可,不必亲自过来。”
长公主更不愿意再驾临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给他一个建议:“你若是愿意听本宫的,时不时回侯府一趟,本宫自然不会再来。还有,你不如尽早换个地方住。”
踏歌也很纳闷,挠了挠头道:“我进去的时候,姑娘自己站起来,让我给她披上衣裳,就出来了。”
沈柔倏然松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拉了拉被子,将自己下半张脸露出来。
卫景朝暼了她一眼,看她眼底的惊惧之色缓缓消散,淡声问:“这次,有脸见人了?”
夕照园从上到下,知道此事的人,没有一个不尴尬的。所以,肯定不会有人再提起此事。
卫景朝没再说什么,脱掉外衫,穿着寝衣躺在她身侧,等她快睡着时,才慢慢开口:“沈柔,你害怕我母亲。”
沈柔怔然,慢慢开了口,“长公主不曾对我做过什么。只是,你或许不记得一件事了。”
“我们刚定亲时,有个丫鬟仗着美貌和身段,想勾引你。”沈柔忍不住打了个冷颤,“长公主命人,生生将她打死,尸体扔在乱葬岗。”
“你这样卑贱的人,也配勾引我的儿子?既然自己不要这条命,我替你丢了,倒也罢了。”
如今她的身份何其卑微,还不如那个丫鬟,若叫长公主知道她与卫景朝勾勾缠缠,恐怕要将她五马分尸,才能泄愤。
“那个丫鬟,不是想爬床。”他淡声解释,“是宫里派来的,想往我的书房里头,放些不该放的东西。”
卫景朝笑了一声,语气里不知道是警告,还是安抚,“只要你不是某些人派来的探子,尽可以放心地活着。”
沈柔垂下眼眸,声音很轻很淡:“我与他们有深仇大恨,纵是死了,也不能为他们所用。”
她带着几分恨,慢慢道:“我父亲被人指认谋逆,从书房里搜出来的东西,想必,也是宫中那位所为吧。”
“是。”沈柔闭上眼,指甲慢慢掐住掌心的肉,竭力按耐住内心的恨。一口气,从腹部舒到胸口,再缓缓吐出来,才松开手。
她之所以畏惧他的母亲,并非是因为亲眼见过对方杀人。京都公侯门第的人,那个没有杀过下人?
她这样自幼长在侯门的女郎,哪怕平南侯府没有这样的事情,她的外祖家,亲朋好友家,总是有的。
她这样聪明,识时务,定是很清楚地知道,一旦与利益相悖,长公主这样冷血的政客,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所有人。
可她终究还是个善良的姑娘,在泥淖中没有选择沉沦,而是独自咽下苦楚,独自承受风雨,从不给任何人带来灾祸。
江燕燕死后,凄惨无比的尸身被送出齐王府,她的父母见状,心肝欲裂。又悲又怒之下告上金銮殿。
这是一个小高潮,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君王能够为民做主,杀了齐王,给江燕燕报仇。
江父忍着丧妻丧子丧女之痛,孤身一人至岭南,却没熬过岭南的瘴气,短短三日,便病终而逝。
没像其他的戏文一样,在故事的最后,出来个义薄云天的青天大老爷,为冤死的人昭雪。
真真这侯门养出来的千金小姐,看上去娇滴滴的,其实个个都是玩弄人心的高手。
可是如今的情况同样让人悲愤难言,平南侯父子冤死北疆,女沈柔死在青楼里,沈夫人被流放边塞,生死未卜。
沈柔温柔一笑,眼底满是感激,只道:“侯爷替我照顾母亲,已是最好的礼物,我别无所求。”
在她心里,母亲的安危,的确是最重要的,解决了心头最大的问题,她便别无所求。
她不敢去看沈柔双眸,心下算了算日子,“我派去找你母亲的人,还需一段时日,才能从北疆回来。”
她的笑容,总是直达眼底,露出脸颊旁浅浅的梨涡,好看又温柔,像是盛满星辰与月光。
卫景朝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避开她风露清愁的眼眸,慢慢道:“你给自己取一个别号,印在书上,以后……”
沈柔坐在椅子上,手里抓着笔,想了半天后,终于苦着脸,仰头看他:“我想不到叫什么才好。”
卫景朝看着她的双眼,略想了想,抬脚走到她身侧,接过她手中的笔,替她在纸上写了两个字。
旁人的笔名,都叫什么先生,什么居士,什么老人,要么便是有一二典故,文雅至极,偏她用这两个常见的字,未免太招人注目了?
沈柔咬着下唇,思考片刻,忽道“又疑瑶台镜,非在青云端,不如就叫瑶台居士吧。”
沈柔点头应了,自己拿起另一支笔,直接在书稿上写,“玉镜先生作于建安二十五年暮春。”
沈柔已经“死”了,若能用玉镜先生的名字,续上未完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一出戏文,从京畿萌芽,比夏日蔓延的速度更快,不过月余光景,四散至朝野内外,全国遍地。
反而是距离京畿最近的京城,到了之后的六月份,才第一次从一个外地来的戏班子里,听到这出戏。
随即,这出戏便风靡京城,引来无数夸赞。而戏文中的两个男人,齐王章昀和江燕燕的未婚夫,则遭到了无数谩骂。
踏歌怒道:“今儿我慕名去听了那出燕燕于飞,真是气死我了。该死的齐王!该死的未婚夫!江燕燕碰上这两个男的,真是晦气,倒霉!”
鹿鸣苑事事都在卫景朝眼皮子底下,她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事儿,他全都一清二楚。
踏歌却误会了,低声道:“姑娘若是也想听戏,不如求一求侯爷,让他将戏班子请到家里头来。”
沈柔的身份,断然不适合出门,否则,但凡被某个曾认识的人看见,就是欺君的死罪。
沈柔摇了摇头:“我没想听戏,只是在想,侯爷今儿没有大朝会,怎么回的这样晚?”
被她惦记着的卫景朝,此时此刻并不在枢密院,而是被同僚们请到戏班子里,坐在雅间里等听戏。
于逸恒笑一声:“昨儿才从江宁府回来。今天慕名来听戏,谁知道一进门先碰上陈大人,就被拉来陪客了。”
卫景朝摇摇头:“这戏文早已在江南传遍,只怕你早就听出花来了,又何必非得来这一趟。”
于逸恒以折扇抵住下巴,如妖似孽的桃花眼微微眯起,漫不经心笑:“戏不戏的不要紧,我主要是想看看,我们背信弃义的未婚夫是个什么表情。”
于逸恒俯身,趴到他跟前,压低了声音问:“说真的,这戏文到底是何方神圣写的?竟将弘亲王、圣上和你一起骂了,胆子大得很啊。”
于逸恒桃花眼迷离带笑,“好弟弟,哥哥我呢,虽然不及你聪明,但也不是个傻子,不至于连一出戏都听不懂。”
他讽刺得毫不留情,“那你说,为什么旁人都不戳破,单你一个人冒头来显摆自己聪明?”
这波人里头,程越年最长,如今也不过不惑之年,陈善舟年三十又八,于逸恒与卫景朝同年,早生了三天,常年以哥哥自居。
先出来的,是扮演江燕燕的花旦,油彩勾勒出少女清丽妩媚的脸庞,身姿窈窕,摇曳生姿,回眸便是国色。
于逸恒笑着打量卫景朝,片刻后凑近他,低声评价道:“这小戏子倒不像你,没有你半分神韵。”
于逸恒嗤了一声:“你再嫌弃我,我就劝长公主,早日给你娶个媳妇,最好是个丑的。”
程越一个三十几岁的大老粗,闻言沉默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于世子,您还年轻,千万别自暴自弃,男人还是要阳刚一些。”
那小生红了脸,回道:“六月上,荷花开,我骑高头大马拜高堂,牵红绫,饮美酒,与你做一个新官郎。”
彼时,他正在苏州游玩,他们见面时,他说等回京便要与沈家女成婚。邀他早日回京,喝他的喜酒。
多年好友,于逸恒看的一清二楚,卫景朝当时是真心实意要娶妻,没有别的算计。
陈善舟的感触,比旁人都深些。大概是因为,真正的“江燕燕”是他看着长大的,世交家的女儿。
昔日里江家遭此大难,他恨不得咬下孟允章的肉,却不得不生生忍下,今日情景再现,怎能不泪流满面。
他盯着楼下的戏台:“若非孟允章行恶,今日的江氏女,也该成婚生子,而非……”
陈善舟终于擦干了眼泪,不敢再听台下戏文,只叹口气,站起身道歉:“本来是说请景朝你们听戏的,只是我这……着实没法子听下去了,今儿先告辞,来日设宴宴请诸位,以作赔罪。”
又过了一会儿,戏文唱到齐王提亲,卫景朝豁然站起身,淡声道:“我有事,先走了。”
————--------------栀子整理——————————————
卫景朝回到鹿鸣苑时,月色已半挂中天,园内一片寂静,只余蝉鸣和蟋蟀窸窣声。
卫景朝推门进来时,她诧异抬眉,半直起身子,朝着他惊讶道:“您怎么回来了?”
所以说,这也怪不得沈柔,实在是有前例在,她多嘴一句,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连忙转移话题:“今天踏歌出去听了燕燕于飞, 侯爷听过吗?外头都怎么说?”
沉默片刻, 他鬼使神差般对她道:“过几天我休沐, 届时带你出去听一场, 你自己亲耳听一听别人的评价。”
她往上动了动身子,从卫景朝肩头爬到与他面对面的位置,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问:“我可以出去吗?会不会有危险?”
她心底极是高兴,本以为能像踏歌说的那样,请戏班子来唱戏,就已经很好很好了。
沈柔不止一次见过,此刻,她微微红了脸,乖乖巧巧在他腿间坐下,依偎进他怀中。
“没……没什么。”沈柔乖乖仰着脸笑,软软道,“您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能起来。”
沈柔裹紧被子,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祈求地看向他,声音越来越低,生怕被旁人听见:“没有受伤。”
进了雅间内,沈柔左右看看,轻声道:“这个地方,颇为清雅,跟一般的戏楼不太一样。”
母女二人自此分离,分离时彼此尚在诏狱中,前路黑暗,不可言说,想必比江燕燕更苦痛几分。
她的母亲在离开之前,挣扎着回头,对女儿说了一句话:“柔儿,来日不管经历什么,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你都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
她甚至来不及多嘱咐半句,说完这句话,诏狱的大门,就再次被关上,隔绝了彼此的视线。
他想,难怪在君意楼这样的地方,她仍旧能够坚强地活下来,为自己寻找一条生路。
沈柔也不语,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杯盏中,泡软了卫景朝的心,泡软了他冰冷的血管。
“什么齐王,莫非你听不出来,这指的就是本朝某些人,还敢骂呢,你也不怕被抓起来!”
“除了他还有谁?昔年兵部侍郎江崇涛的女儿,你们都忘了不成?这出戏文,活脱脱指的就是这件事儿,外地人不知道,咱们京城里难道还有人不知道?”
“这算什么胆大,这出戏在外地早就红翻天了,咱们京城也只是跟风罢了!大不了关门不唱了,还能怎么办?”
“这里不正是平南侯府沈姑娘的事儿吗?前些日子,长陵侯冲冠一怒为红颜,咱们还夸他有英雄气概。”
“不得不说,那长陵侯的确比江燕燕的未婚夫强多了,能为了惨死的未婚妻出头,得罪权贵,得罪皇帝,是个铁骨铮铮的真汉子。”
“那怎么能比?长陵侯也是朝中一等一的权贵,是圣上的亲外甥,自然敢得罪弘亲王。”
“你若这么说,那更不能比了。江燕燕无辜惨死,为她出头天经地义。那平南侯之女却是逆臣,朝中都说死不足惜,长陵侯却仍惦记着旧日情分,冒着杀头的风险为她出头,如此情深义重,谁人能比?”
如今戏文一出,旁人不会觉得江燕燕的未婚夫是他,只会觉得,相比之下,他真是人间难得的好男人。
他抬眼望去,只见从门外哗啦啦跑进来一对官兵,穿着京兆府捕快的服饰,腰间挎着刀,训练有素地站成两排。
开门见山道:“本官奉命查办违禁戏文,配合的,重重有赏。若是不配合,京兆府的板子可不认人。”
他坐在椅子上,拍了拍扶手,先问一旁的鬓发皆白的老人家,“老爷子,你们今天在这儿听的什么戏啊?”
老爷子眉目慈祥,慢吞吞抚着胡须,道:“今日听的,是一出感天动地窦娥冤,这窦娥真是个可怜人,少年丧母,被父所卖……”
“好了!”府尹打断他,“本官知道窦娥冤讲的什么。你说,今天听的是什么戏。”
男子手持折扇,一派风流潇洒,笑吟吟道:“自然是窦娥冤,这窦娥冤情太大了,看的我是心潮彭拜,恨不得斩杀狗官!”
“张府尹要问谁?”卫景朝淡声开口,抬脚拦在沈柔面前,语气平静,“舍妹年少不懂事,府尹不如问问我。”
卫景朝居高临下看着他,神色漠然:“今日听的是窦娥冤,并无什么违禁戏文,张府尹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张府尹哪儿敢跟他别苗头,连忙道:“侯爷说的是,这家并没有什么违禁戏文,下官这就带人去下一家,这就走。”
而且,张府尹已等不及底下人去查封,给他汇报,自己亲自带人一家一家查问,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封。
“若仅仅是西城的戏班子,应该差不多。”沈柔道,“这些戏班子都正经在衙门有文书,好找好查。但东城那边都是普通百姓,唱戏的也都是临时组的班子、台子,唱完一场就换地方,若要想查封他们,比登天还难。”
他撩开马车的帘子,望着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道:“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没有人能彻底消灭。”
不出所料, 短短三天,西城所有的戏班子都严禁再唱这出火遍大江南北的《燕燕于飞》。
可是,东城的街头巷尾, 却多了些草台班子,慢悠悠唱着戏,官兵一来,抄着头面跑的比谁都快。
短短月余,满京百姓的话题,都围绕着弘亲王展开。也因着弘亲王的缘故, 对皇室, 对皇帝都多了几分不满。
这个结果, 令宫中的君王十分震怒, 命令京兆府协同刑部,一定要查出这戏文的来源,查出那位“玉镜先生”, 到底是何方神圣。
张府尹苦着脸道:“陛下, 这出戏文从京畿散至全国各地,数月后才传进京城,臣派人去京畿打听, 都说当时给他们戏文的人, 早就离开了。”
“而且, 不同的戏班子, 描述出来的样貌都不一样。现如今,除了知道这位玉镜先生是位约摸弱冠的书生外,再无其他消息。”
查这样的案子,向来都无异于大海捞针。要从茫茫人海里找一个没有特点,没有样貌,没要名字的人,谈何容易。
“这出戏臣亦听过,写的荡气回肠,文采精华,气势不俗。”他每夸一句,皇帝的脸便黑沉三分。卫景朝权当没看见,继续道:“由此可见,这位玉镜先生定是个年少轻狂的饱学之士,不如全面排查全天下年轻的有才书生,定能找到此人。”
“这些个书生,个个都要面子,个个都自诩尊贵,若是如此,只怕要得罪全天下的书生。”
如此一来,所有人都会认为,玉镜先生是个年轻书生了。谁也不会想到,是他藏在鹿鸣苑里的沈柔。
皇帝不耐烦道:“行了,都回去想想法子,不将这个玉镜先生抓回来碎尸万段,朕绝不罢休。”
“玉镜先生在戏文里的遣词用句,颇有岭南风格,臣以为这位玉镜先生,说不定是岭南人。”
“景朝果然学富五车,竟连岭南戏都有所涉猎,若非你近日没出过京,朕都要怀疑,这戏文是你所写了。”
然而,卫景朝依然不卑不亢,掸了掸衣袖,傲然道:“那陛下未免太看不起臣了。若臣执笔写戏文,定非这玉镜先生可比。”
他眼角眉梢俱是少年傲气,甚至敢反问高高在上的君王:“莫非陛下觉得,臣的水平仅仅如此吗?”
倏然,皇帝大笑一声,从高台上走下来,拍了拍卫景朝的肩膀:“朕与你开玩笑,千万别当真。”
皇帝哼笑一声,拿手指指了指一圈人:“你们都跟景朝学着点,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别总是尸位素餐,惹人心烦。”
待走出御书房后,陈善舟摘下官帽,狠狠地抹了把额头,将额上的汗液抹了个干净,才劫后余生般道:“你怎么这样大胆,什么话都敢说,若是……”
罢了罢了,这年轻人,总有一天会认清现实,认清楚,他们的帝王,并非一位清正严明的好皇帝。
卫景朝道:“圣上慧眼如炬,定能洞若观火,不会怀疑我的,陈大人尽管放心。”
他从不会将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里头,敢说这样的话,便是出于对皇帝过分的了解。
皇帝的疑心病之重,几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如今倒不显,等以后京兆府百般查不到“玉镜先生”是何人时,他的疑心病,肯定会转到朝堂上来。
与其等到那时候无端被疑,不如先站出来,主动让皇帝生了疑心,之后再让他自己通过查证,打消疑虑。
如此一来,圣上自己先生出三分信任,以后任是谁再往他头上泼脏水,都没有用处。
陈善舟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又叹了口气:“不知这位玉镜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竟如此胆大妄为,若真被京兆府抓着了,恐怕……”
卫景朝声音淡泊:“那也要京兆府能抓到人才好,这位玉镜先生眼看着便不是寻常人物,来无影去无踪的,又千变万化的,过了这样久,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言之有理。”陈善舟感慨万千,忍不住道,“一时之间,竟不知是该盼着他被抓,还是不被抓了。”
沈柔默默盯着他,一双清凌凌的眸子,带上三分委屈三分埋怨,像是被他这反应伤到了。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铺垫,开门见山道:“今天叫你过来,是因为我派去看你母亲的人,今天早上刚从北疆回来。”
沈柔顿时顾不上其他,手指微颤,竭力遏制住自己的激动,问他:“我阿娘……怎么样了?”
卫景朝继续道:“你母亲被流放去了凉州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如今情形尚可。”
凉州境内的官兵与百姓,无一不感念平南侯的恩情,母亲至此,应当过的还可以。
卫景朝顿了顿,道:“但你母亲毕竟年岁大了,流放时天气又冷,初至凉州时大病一场,好在凉州百姓对她不错,延医问药,多方照顾,如今已大安。”
沈柔听到母亲大病一场时,眼底就已蓄满泪水,屏着呼吸,才克制住眼泪夺眶而出。
人也坐不住了,从椅子上滑落下去,蹲在地上,头埋在膝盖中间,整个人蜷缩成一小团。
卫景朝并不瞒着她,垂眸道:“病已好,人也在凉州安了家,活下去是没问题,只是与以前没法比,听说如今极是瘦弱,也自己干起了粗活,下地洗衣做饭,样样都得自己做。”
她的母亲,以往是养尊处优的侯夫人,身娇体弱,十指纤纤,如今却大病一场,弱不胜衣,还要自己下地,洗衣服,做饭。
其实,现在这样已是最好的结果,比之流放至岭南、西南,乃至于任何其他地方,都已经是件好事了。
他只能冷下脸,忘掉心底的痛楚,唇角含着温润笑意,哪怕在生父的葬礼上,也要做一个合格的“侯爷。”
直到她渐渐止住哭声,卫景朝才继续道:“我的人给她送了衣物,粮食,银两和药材,帮她建了房子,又打了一口井,才从凉州回来,可以确保她下个冬天好好活下去,你可以放心。”
他望着沈柔的眼睛,眼底是一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疼惜,“沈柔,我会让你母亲好好活下去的,你不需要哭。”
她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猛然抬手抱住他的脖子,将头埋进他怀中,眼泪蹭在他衣襟上。
抬手将她整个抱起来,放在一旁的椅子上,低头鬼使神差道:“真的难受,就哭吧。”
夏日里的阳光灿烂热烈,透过层层叠叠的梧桐叶,变成稀碎的光斑落在地上,洒入窗棂中。